有朋自遠方來一一專訪 Constantine M
Total Page:16
File Type:pdf, Size:1020Kb
Load more
Recommended publication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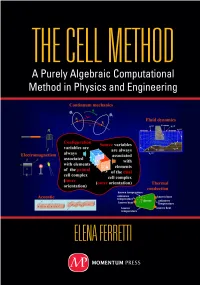
The Cell Method: a Purely Algebraic Computational Method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Copyright © Momentum Press®, LLC, 2014
THE CELL METHOD THE CELL METHOD A PURELY ALGEBRAIC COMPUTATIONAL METHOD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ELENA FERRETTI MOMENTUM PRESS, LLC, NEW YORK The Cell Method: A Purely Algebraic Computational Method in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Copyright © Momentum Press®, LLC,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any other—except for brief quotations, not to exceed 400 word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First published by Momentum Press®, LLC 222 East 46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www.momentumpress.net ISBN-13: 978-1-60650-604-2 (hardcover) ISBN-10: 1-60650-604-8 (hardcover) ISBN-13: 978-1-60650-606-6 (e-book) ISBN-10: 1-60650-606-4 (e-book) DOI: 10.5643/9781606506066 Cover design by Jonathan Pennell Interior design by Exeter Premedia Services Private Ltd. Chennai, India 10 9 8 7 6 5 4 3 2 1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TENTS ACKNOWLEDGMENTS vii PREFACE ix 1 A COMpaRISON BETWEEN ALGEBRAIC AND DIFFERENTIAL FORMULATIONS UNDER THE GEOMETRICAL AND TOPOLOGICAL VIEWPOINTS 1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How to Compute Limits and Numerical Formulations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 2 1.1.1 Some Basics of Calculus 2 1.1.2 The e − d Definition of a Limit 4 1.1.3 A Discussion on the Cancelation Rule for Limits 8 1.2 Field and Global Variables 15 1.3 Set Functions in Physics 20 1.4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ell Method and the Discrete Methods 21 2 ALGEBRA AND THE GEOMETRIC INTERPRETATION -

Writing the History of Dynamical Systems and Chaos
Historia Mathematica 29 (2002), 273–339 doi:10.1006/hmat.2002.2351 Writing the History of Dynamical Systems and Chaos: 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Longue at core.ac.uk Dur´ee and Revolution, Disciplines and Cultures1 brought to you by CORE provided by Elsevier - Publisher Connector David Aubin Max-Planck Institut f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Berlin, Germany E-mail: [email protected] and Amy Dahan Dalmedico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and Centre Alexandre-Koyre,´ Paris, France E-mail: [email protected]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he wide recognition that simple dynamical laws could give rise to complex behaviors was sometimes hailed as a true scientific revolution impacting several disciplines, for which a striking label was coined—“chaos.” Mathematicians quickly pointed out that the purported revolution was relying on the abstract theory of dynamical systems found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by Henri Poincar´e who had already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flesh out the historiographical tensions arising from these confrontations: longue-duree´ history and revolution; abstract mathematics and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in various other domains. After reviewing the historiography of dynamical systems theory from Poincar´e to the 1960s, we highlight the pioneering work of a few individuals (Steve Smale, Edward Lorenz, David Ruelle). We then go on to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 chaos phenomenon, which, we argue, was a conceptual reconfiguration as -

Homogenization 2001,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HMS2000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Conference on Ho- Mogenization
in \Homogenization 2001,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HMS2000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Conference on Ho- mogenization. Naples, Complesso Monte S. Angelo, June 18-22 and 23-27, 2001, Ed. L. Carbone and R. De Arcangelis, 191{211, Gakkotosho, Tokyo, 2003". On Homogenization and Γ-convergence Luc TARTAR1 In memory of Ennio DE GIORGI When in the Fall of 1976 I had chosen \Homog´en´eisationdans les ´equationsaux d´eriv´eespartielles" (Homogenization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for the title of my Peccot lectures, which I gave in the beginning of 1977 at Coll`egede France in Paris, I did not know of the term Γ-convergence, which I first heard almost a year after, in a talk that Ennio DE GIORGI gave in the seminar that Jacques-Louis LIONS was organizing at Coll`egede France on Friday afternoons. I had not found the definition of Γ-convergence really new, as it was quite similar to questions that were already discussed in control theory under the name of relaxation (which was a more general question than what most people mean by that term now), and it was the convergence in the sense of Umberto MOSCO [Mos] but without the restriction to convex functionals, and it was the natural nonlinear analog of a result concerning G-convergence that Ennio DE GIORGI had obtained with Sergio SPAGNOLO [DG&Spa]; however, Ennio DE GIORGI's talk contained a quite interesting example, for which he referred to Luciano MODICA (and Stefano MORTOLA) [Mod&Mor], where functionals involving surface integrals appeared as Γ-limits of functionals involving volume integrals, and I thought that it was the interesting part of the concept, so I had found it similar to previous questions but I had felt that the point of view was slightly different. -

Mathematics to the Rescue Retiring Presidential Address
morawetz.qxp 11/13/98 11:20 AM Page 9 Mathematics to the Rescue (Retiring Presidential Address) Cathleen Synge Morawetz sh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lecture to my tial equation by a simple difference scheme and get- teacher, Kurt Otto Friedrichs. While many ting nonsense because the scheme is unstable. people helped me on my way professionally, The answers blow up. The white knights—Courant, Friedrichs played the central role, first as my Friedrichs, and Lewy (CFL)—would then step in thesis advisor and then by feeding me early and show them that mathematics could cure the Iresearch problems. He was my friend and col- problem. That was, however, not the way. But first, league for almost forty years. As is true among what is the CFL condition? It says [1] that for sta- friends, he was sometimes exasperated with me (I ble schemes the step size in time is limited by the was too disorderly), and sometimes he exasperated step size in space. The simplest example is the dif- me (he was just too orderly). However, I think we ference scheme for a solution of the wave equa- appreciated each other’s virtues, and I learned a tion great deal from him. utt uxx =0 Sometimes we had quite different points of − view. In his old age he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on a grid that looks like the one in Figure 1. Sec- at Jack Schwartz’s request, for archival purposes. ond derivatives are replaced by second-order I was the interviewer. At one point I asked him differences with t = x. -

Saul Abarbanel SIAM Oral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SAUL ABARBANEL Conducted by Philip Davis on 29 July, 2003, at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Brown Universit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as part of grant # DE-FG02-01ER25547 award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Transcript and original tapes donated to 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by the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 Computer History Museum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ABSTRACT: ABARBANEL describes his work in numerical analysis, his use of early computers, and his work with a variety of colleagu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barbanel was born and did his early schooling in Tel Aviv, Israel, and in high school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After serving in the Israeli army, Abarbanel entered MIT in 1950 as an as an engineering major and took courses with Adolf Hurwitz, Francis Begnaud Hildebrand, and Philip Franklin. He found himself increasing drawn to applied mathematics, however, and by the time he began work on his Ph.D. at MIT he had switched from aeronautics to applied mathematics under the tutelage of Norman Levinson. Abarbanel recalls the frustration of dropping the punch cards for his program for the IBM 1604 that MIT was using in 1958 when he was working on his dissertation, but also notes that this work convinced him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uters. Abarbanel also relates a humorous story about Norbert Weiner, his famed linguistic aptitude, and his lesser-known interest in chess. Three years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Abarbanel returned to Israel, where he spent the rest of his career at Tel Aviv University. -

Glimm and Witten Receiv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Volume 51, Number 2
Glimm and Witten Receiv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On October 22, 2003, President Bush named eight of the nation’s leadi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o receive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The medal is the nation’s highest honor for achievement in sci- ence,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The medal James G. Glimm Edward Witten also recognizes contributions to innovation, in- dustry, or edu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59. He is the Distin- Among the awardees are two who work in the guished Leading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JAMES G. GLIMM and EDWAR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WITTEN. Edward Witten James G. Glimm Witten is a world leader in “string theory”, an attempt Glimm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by physicists to describe in one unified way all the shock wave theory, in which mathematical models known forces of nature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natural phenomena that nature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Witten’s contributions involve intense compression, such as air pressure while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have set in sonic booms, crust displacement in earthquakes, the agenda for many developments, such as progress and density of material in volcanic eruptions and in “dualities”, which suggest that all known string other explosions. Glimm also has been a leading theories are related. theorist in operator algebras, partial differential Witten’s earliest papers produced advances in equations, mathematical physics, applied mathe- quantum chromodynamics (QCD), a theory that matics, and quantum statistical mechanics.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fundamental Glimm’s work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and particles (quarks and gluons) that make up all statistical mechanics had a major impact on atomic nuclei. -

Peter D. Lax: a Life in Mathematics
Peter D. Lax: A Life in Mathematics There is apparently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mathematical contributions of Peter Lax and his effect on the work of so many others that has not already been said in several other places, including the Wikipedia, the web site of the Norwegian Academy’s Abel Prize, and in quite a few other tributes. These lines are being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Peter’s 90th birthday — which will be mathematically celebrated at the 11th AIMS Conference on Dynamical System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be held in July 2016 in Orlando, FL — and their author merely intends to summarize some salient and relevant points of Peter’s life and work for this celebration. The Life. Peter was born on May 1st, 1926 into an upper-middle class, highly educated Jewish family in Budapest, Hungary. Fortunately for him, his family realized early on the danger to Jewish life and limb posed by the proto-fascist government of Miklós Horthy, a former admiral in the Austro-Hungarian Navy, who ruled the country from March 1920 to October 1944 with the title of Regent of the Kingdom of Hungary. The Laxes took the last boat from Lisbon to New York in November 1941. In New York, Peter completed his high-school studies at the highly competitive Stuyvesant High School and managed three semesters of mathematic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before being drafted into the U.S. Army. His mathematical talents were already recognized by several leading Jewish and Hungarian mathematicians who had fled the fascist cloud gathering over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cluding Richard Courant at NYU and John von Neumann at Princeton. -

Kurt Otto Friedrichs Selecta Volume 1
birkhauser-science.de Scienc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ultidisciplinary : Scienc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ultidisciplinary Morawetz, C.S. (Ed.) Kurt Otto Friedrichs Selecta Volume 1 In 1981 I was approached by Klaus Peters to assist in publishing a selection of the papers of Kurt Otto Friedrichs. With some reluctance Friedrichs has agreed to help in making the selection although in the initial stages only one paper [47-2] was in his opinion worthy of being included. With some coaxing on my part the selection was made mainly by Friedrichs despite his frequent modest grumble that it did not make sense to include "that" paper as "X" had subsequently improved either the result or the proof. Later P.O. Lax and L. Nirenberg identified appropriate papers and, perhaps not so remarkably, there was almost complete overlap.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apers are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spectral theory where Friedrichs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For these Peter Lax and Tosio Kato have written the commentaries. Friedrichs mad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in the theory of asymptotics; two Birkhäuser papers, including Friedrichs' Gibbs Lecture, have been reviewed by W. Wasow. The very 1986, 427 p. 2 illus. profound contributions Friedrichs made to applied mathematics are represented by some 1st papers in elasticity, mainly written with J.J. Stoker and now reviewed by F. John and in edition magneto-hydrodynamics where Friedrichs' original notes have been reproduced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ubject reviewed by Harold Weitzner. -

What Is Mathematics, Really? Reuben Her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What Is Mathematics, Really? Reuben Her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o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Copyright © 1997 by Reuben Hersh First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First issued as 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99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Hersh, Reuben, 1927- What is mathematics, really? / by Reuben Hersh. p. cm.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ISBN 0-19-511368-3 (cloth) / 0-19-513087-1 (pbk.) 1. Mathematics--Philosophy. I. Title. QA8.4.H47 1997 510 ′.1-dc20 96-38483 Illustration on dust jacket and p. vi "Arabesque XXIX" courtesy of Robert Longhurst. The sculpture depicts a "minimal Surface" named after the German geometer A. Enneper. Longhurst made the sculpture from a photograph taken from a computer-generated movie produced by differential geometer David Hoffman and computer graphics virtuoso Jim Hoffman. Thanks to Nat Friedman for putting me in touch with Longhurst, and to Bob Osserman for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The "Mathematical Notes and Comments" has a section wit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inimal surfaces. Figures 1 and 2 were derived from Ascher and Brooks, Ethnomathematics , Santa Rosa, CA.: Cole Publishing Co., 1991; and figures 6-17 from Davis, Hersh, and Marchisotto, The Companion Guide to the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 Cambridge, Ma.: Birkhauser, 1995. -

KURT OTTO FRIEDRICHS September 28, 1901–January 1, 198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K U R T O T T O F RIEDRIC H S 1901—1983 A Biographical Memoir by CATH L E E N S YNG E MORA W ETZ Any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memoir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iographical Memoir COPYRIGHT 1995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 D.C. KURT OTTO FRIEDRICHS September 28, 1901–January 1, 1983 BY CATHLEEN SYNGE MORAWETZ HIS MEMORIAL OF Kurt Otto Friedrichs is given in two Tparts. The first is about his life and its relation to his mathematics.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his work, which spanned a very great variety of innovative topics where the innovator was Friedrichs. PART I: LIFE Kurt Otto Friedrichs was born in Kiel, Germany, on Sep- tember 28, 1901, but moved before his school days to Düsseldorf. He came from a comfortable background, his father being a well-known lawyer. Between the views of his father, logical and, on large things, wise, and the thought- ful and warm affection of his mother, Friedrichs grew up in an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math- ematics and philosophy. Despite being plagued with asthma, he completed the classical training at the local gymnasium and went on to his university studies in Düsseldorf. Follow- ing the common German pattern of those times, he spent several years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Most strikingly for a while he studied the philosophies of Husserl and Heidegger in Freiburg. He retained a lifelong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of philosophy but eventually decided his real bent was in math- 131 132 BIOGRAPHICAL MEMOIRS ematics. -

Selected Papers of Peter Lax, Peter Sarnak and Andrew Majda (Editors), Springer, 2005, Xx+620 Pp., US$119.00, ISBN 0-387-22925-6
BULLETIN (New Seri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Volume 43, Number 4, October 2006, Pages 605–608 S 0273-0979(06)01117-7 Article electronically published on July 17, 2006 Selected papers of Peter Lax, Peter Sarnak and Andrew Majda (Editors), Springer, 2005, xx+620 pp., US$119.00, ISBN 0-387-22925-6 Peter Lax’s mathematical work is a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prewar Budapest and postwar New York. By Budapest, I mean his elegant geometric, functional- analytic style of attacking hard, concrete problems. By New York or NYU, I mean his lifelong interest in physics and in practical computation. Like Peter’s idol Johnny von Neumann (Neumann Jancsi at home), Peter’s education benefited from the prewar Budapest institution of home tutoring by unemployed mathemat- ical geniuses. For Johnny, it was Gabor Szeg¨o and Michael Fekete; for Peter, it was Rozsa Peter. He said, “The very first thing we did was to read The Enjoyment of Mathematics by Rademacher and Toeplitz. I was twelve or thirteen. ...I went to her house twice a week for a period of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left Hungary at fifteen and a half.” The Laxes sailed from Lisbon on the fifth of December 1941, two days before the Japanese attacked Pearl Harbor and brought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ar. When the Laxes arrived in New York, Richard Courant had been forewarned. “My Hungarian mentors were von Neumann and Szeg¨o; it was Szeg¨o who suggested that I study with Courant.” In 1986, in Tokyo en route to Palo Alto, I bumped into P´al Erd¨os. -

Biographical Memoirs V.67
This PDF is available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at 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4894 Biographical Memoirs V.67 ISBN Office of the Home Secretar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78-0-309-05238-2 404 pages 6 x 9 HARDBACK (1995) Visit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online and register for... Instant access to free PDF downloads of titles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MEDICIN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0% off print titles Custom notification of new releases in your field of interest Special offers and discounts Distribution, posting, or copying of this PDF is strictly prohibi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ll materials in this PDF are copyrigh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Request reprint permission for this book Copyright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ll rights reserved. Biographical Memoirs V.67 i Biographical Memoir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uthoritative version for attribution. ing-specific formatting, however, cannot be About PDFthis file: This new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original workthe has been recomposed XMLfrom files created from original the paper book, not from the original typesetting files. breaks Page are the trueline lengths, word to original; breaks, heading styles, and other typesett aspublication this inserted. versionofPlease typographicerrors have been accidentallyprint retained, and some use the may Copyright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ll rights reserved. Biographical Memoirs V.67 About this PDF file: This new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work has been recomposed from XML files created from the original paper book, not from the original typesetting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