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 ——以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 讨(1928-1941) 文 / 王 皓
Total Page:16
File Type:pdf, Size:1020Kb
Load more
Recommended publications
-

Inventory Acc.13559 Reverend James Watson
Acc.13559 March 2015 Inventory Acc.13559 Reverend James Watson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Manuscripts Division George IV Bridge Edinburgh EH1 1EW Tel: 0131-623 3876 Fax: 0131-623 3866 E-mail: [email protected] ©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Papers, 1894-1942, of Rev James Watson, missionary with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China. Papers of Reverend James Watson (1878-1954),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BMS), originally from Wishaw, Lanarkshire. The papers consist mostly of Watson‟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service in China from 1906 to the 1930s, but especially concerning hi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siege of Xi'an, Shaanxi province, April-November 1926. The collection also contains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Watson and his family. The main family personalities covered by the papers are James Watson, his wife Evelyn (née Evelyn Minnie Russell), thei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John, Helen, Wreford (who went on to be a noted geograp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argaret and Andrew. Some other relatives appear in the papers as correspondents or mentioned in letters. A number of leading BMS missionaries in Xi'an and elsewhere also appear as correspondents or mentioned in letters, including A.G. Shorrock, John Shields, Clement Stockley, E.L. Phillips, Frederick Russell (also brother of Evelyn), William Mudd, and Jennie Beckingsale. The mission stations, schools and hospital in Xi'an, and other mission stations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yside of Shaanxi province, were one of two major centres of BMS activity in China, the other be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Shaanxi work began in 1890, and the BMS workers were caught up in both the Boxer Rebellion of 1900-01 (during which around 40 BMS missionarie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killed in Shaanxi)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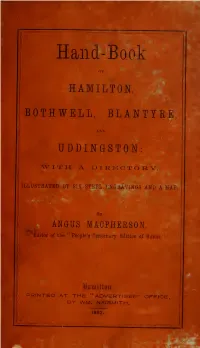
Hand-Book of Hamilton, Bothwell, Blantyre, and Uddingston. with a Directory
; Hand-Book HAMILTON, BOTHWELL, BLANTYRE, UDDINGSTON W I rP H A DIE EJ C T O R Y. ILLUSTRATED BY SIX STEEL ENGRAVINGS AND A MAP. AMUS MACPHERSON, " Editor of the People's Centenary Edition of Burns. | until ton PRINTED AT THE "ADVERTISER" OFFICE, BY WM. NAISMITH. 1862. V-* 13EFERKING- to a recent Advertisement, -*-*; in which I assert that all my Black and Coloured Cloths are Woaded—or, in other wards, based with Indigo —a process which,, permanently prevents them from assuming that brownish appearance (daily apparent on the street) which they acquire after being for a time in use. As a guarantee for what I state, I pledge myself that every piece, before being taken into stock, is subjected to a severe chemical test, which in ten seconds sets the matter at rest. I have commenced the Clothing with the fullest conviction that "what is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 to accomplish which I shall leave " no stone untamed" to render my Establishment as much a " household word " ' for Gentlemen's Clothing as it has become for the ' Unique Shirt." I do not for a moment deny that Woaded Cloths are kept by other respectable Clothiers ; but I give the double assurance that no other is kept in my stock—a pre- caution that will, I have no doubt, ultimately serve my purpose as much as it must serve that of my Customers. Nearly 30 years' experience as a Tradesman has convinced " me of the hollowness of the Cheap" outcry ; and I do believe that most people, who, in an incautious moment, have been led away by the delusive temptation of buying ' cheap, have been experimentally taught that ' Cheapness" is not Economy. -

T. F. Torrance on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a Biographical and Theological Synopsis with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 F. TORRANCE ON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A BIOGRAPHICAL AND THEOLOGICAL SYNOPSIS WITH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omas A. Noble,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Nazarene Theological Seminary Senior Research Fellow in Theology, Nazarene Theological College, Manchester [email protected] Abstract: Given as a lecture at the meeting of the T. F. Torrance Theological Fellowship on 21st November, 2013, this paper celebrates the centenary of Torrance’s birth. It begins with the world into which he was born and the ethos of 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movement to which his family belonged. Major aspects of his thinking are considered against his biographical background as they became promin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eology: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nd his ecumenical endeavours, his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scientic metho of theolog in relation to the natural sciences his focus on the Incarnation and the Atonement, his engagement with the Greek Fathers, and his place in the Trinitarian revival. The review of Torrance’s thought is interspersed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from several years as Torrance’s student at New College, Edinburgh in the 1970s and from later contact. To return in thought to 1913, the year in which T. F. Torrance was born, is to return to another world. The German Kaiser, the Austrian Kaiser, the Czar of all the Russias, and the Sulta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ll still ruled – not to mention his Britannic Majesty, King George V, Emperor of India, presiding over the largest empire the world had ever seen. His Royal Navy dominated the oceans of the world and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abolishing piracy and the slave trade for ever (or so it was thought). -

Fine Chinese Art New Bond Street, London I 16 May 2019
Fine Chinese Art New Bond Street, London I 16 May 2019 84 (detail) 130 (detail) Fine Chinese Art New Bond Street, London I Thursday 16 May 2019 10.30am (lots 1 - 128) 2pm (lots 129 - 279) VIEWING GLOBAL HEAD, CUSTOMER SERVICES As a courtesy to intending Saturday 11 May CHINESE CERAMICS Monday to Friday 8.30am - 6pm bidders, Bonhams will provide a 11am - 5pm AND WORKS OF ART +44 (0) 20 7447 7447 written Indication of the physical Sunday 12 May Asaph Hyman condition of lots in this sale if a 11am - 5pm Please see page 4 for bidder request is received up to 24 hours before the auction starts. Monday 13 May ENQUIRIES information including after-sale 9am - 7.30pm collection and shipment This written Indication is issued Colin Sheaf subject to Clause 3 of the Notice Tuesday 14 May +44 (0) 20 7468 8237 拍賣品之狀況 to Bidders. 9am - 4.30pm [email protected] Wednesday 15 May 請注意: 本目錄並無說明任何拍賣 品之狀況。按照本目錄後部份所載 9am - 4.30pm Asaph Hyman REGISTRATION 之「競投人通告第 條 」, 準 買 家 +44 (0) 20 7468 5888 15 IMPORTANT NOTICE 必須拍賣前親自確定拍賣品之狀 SALE NUMBER [email protected] Please note that all customers, 況。 irrespective of any previous 25357 純為方便準買家,本公司如果拍買 Benedetta Mottino activity with Bonhams, are 開始前24小時收到準買家的要求, +44 (0) 20 7468 8236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Bidder CATALOGUE 本公司可提 供 書面上的 狀 況 報 告。 [email protected] Registration Form in advance of £30.00 該報告是依據「競投人通告第1.6 條 」提 供。 the sale. The form can be found BIDS Edward Luper at the back of every catalogue +44 (0) 20 7468 5887 +44 (0) 20 7447 7447 ILLUSTRATIONS and on our website at www.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Japan and Corea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 JAPAN AND COREA FOR THE YEAR 1904 HONGKONG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 DAILY PRESS ” OFFICE 14, DES VEUX ROAD CENTRAL LONDON OFFICE : 131, FLEET STREET , E.C. MDCCCCIV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ALLGEMEINER EVANGELISCH PRO Rev. C. A. Salquist and wife (atsent ) 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Rev. R. Wellwood and wife ( GENERAL PROTESTANT MISSION YACHOW VIA CHUNGKING OF GERMANY) Rev. W. M. Upcraft , D.D. TSINGTAU Rev. Briton Corlies, M.D. Rev. R. Wilhelm and wife SWATOW , Rev. B Blumhardt Rev. Wm . Ashmore , D.D. , and wife (absent ) E. Dipper , M.D. Rev. S. B. Partridge, D.1 ., and wife Rev. G. H. Waters and wife AMERICAN ADVENT CHRISTIAN Mrs. A. K. Scott, M.D. MISSION Rev. Wm . Ashmore , Jr., M.A. and wife NANKING Rev. J. M. Foster, M.A. , and wife (absent) Rev. G. Howard Malone and wife ( absent ) Robert E. Worley, M.D. , and wife Miss Margaret B. Burke Miss H. L. Hyde Miss Nellie E , Dow Miss M. Sollman WUHU Miss M. F. Weld Rev. Z. Charles Beals and wife KAYIN VIA SWATOW Rev. G. E. Whitman and wif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Rev. S. R. Warburton and wife UNION CHAOCHOWFU VIA SWATOW HANYANG VIA HANKOW Rev. H. A. Kemp and wife Rev. J. S. Adams and wife UNGKUNG VIA SWATOW Rev. G. A. Huntley , M.D. , and wife (absent ) Rev. J. W. Carlin , D.D. , and wife Rev. Sidney G. Adams KITYANG VIA SWATOW Miss Annie L. Crowl ( absent ) Rev. Joseph Speicher and wife HANGCHOW VIA SHANGHAI Miss Josephine M. Bixby , M.D. -

Thomas F. Torrance and the Chinese Church
The missional nature of divine-human communion: Thomas F. Torrance and the Chinese church CG Seed 24135984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Doctor Philosophiae in Dogmatics at the Potchefstroom Campus of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Promoter: Prof Dr DT Lioy Co-Promoter: Prof Dr PH Fick MAY 2016 PREFA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Daniël Lioy and Professor Rikus Fick for acting as promoters for this research. Their guidance and advice the whole length of the journey has been invaluable. In addition,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t Greenwich School of Theology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have been a constant source of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for which I am grateful. Ken Henke and his team of archivists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T.F. Torrance Manuscript Collection provided professional support and a positive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undertake the primary research. I am grateful too to the Church Mission Society for allowing me study leave in the USA and to Professor David Gregory-Smith for making the trip possible. Thanks are also due to my brother, Mark Streater and his wife Diana in Connecticut, for hosting me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back up. My husband, Rev Dr Richard Seed, has accompanied me along the academic journey, providing moral encouragement and practical support in more ways than can be documented here. I could not have completed the work without him. Thanks are also due to friends in London who offered me accommodation while I was working in the British Library, to our son Richard and his wife Jess for accommodation while I was working at Tyndale House in Cambridge. -

Issionaryresearch Of
Vol. 8, No.2 nternattona• April 1984 ett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Mission ow to relate the universality of God's revealing and undoubtedly will need to speak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 redeeming activity among all nations and people to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mission in still different ways. particularity of God's saving action in Israel and in Jesus Christ is an Even when that happens, some of the benchmarks from the past issue that has been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 will be of lasting value. miss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criptures of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speak to this problem, and Christians in every age have had to wrestle with it anew. This issue of the On Page International Bulletin approaches this enduring problem from several different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50 Roman Catholic Approaches to Other Religions: Paul F. Knitter surveys the different Roman Catholic ap Developments and Tensions proaches to other religions, and indicates how the various schools PaulF. Knitter of missiologists have tried to deal with universal truth that is pres ent in all religions and the particular affirmations of Christian 54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Continuity and tradition. Discontinuity W. S. Campbell examines the specific relations between W S. Campbell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in term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A basic question is to what extent Paul saw the Gentile Christians 59 Eastern Orthodox Mission Theology as displacing Israel as the people of God, and thus overcoming one James Stamoolis form of particularity with another. In the Eastern Orthodox tradition, as James Stamoolis points 63 Pioneers in Mission: Zinzendorf and the Moravians out,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come together in their views of David A. -
Chinese-English Glossary
Chinese-English Glossary Listed below is a 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 and name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heir common English renderings. The romanization is always given in Pinyin with alternative renderings given in parenthese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give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ystem. Glossary of Chinese Terms and Names Phonetic Rendering(s) Chinese Characters English Rendering baihua 䘥娙! ! vernacular Chinese language ben-mo 㛔㛓 beginning and end bense jiaohui 㛔刚㔁㚫 indigenous church Chen Chonggui 昛ⲯ㟪 Marcus Cheng (1884–1963) Chen Duxiu 昛䌐䥨 Chen Duxiu (1879–1942) (Chen Tu-hsiu) chengyu ㆸ婆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or proverbial phrase dangdai xin rujia / 䔞ẋ㕘₺⭞ / Contemporary dangdai xin ruxue !䔞ẋ㕘₺⬠ Neo-Confucianism Dao (Tao)忻 the Way daojia 忻⭞ philosophical Daoism daojiao 忻㔁 religious Daoism Deng Xiaoping 惏⮷⸛ Deng Xiaoping (1904–1997) Di ⛘ Earth di er ci qimeng 䫔Ḵ㫉! ┇!呁 Second Enlightenment / Seco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Ding Guangxun ᶩ妻 K. H. Ting (1915–) (Ting Kuang-hsun) Du Weiming (Tu Wei-ming)㜄䵕㖶 Tu Wei-ming (1940–) Fang Dongmei 㕡㜙伶 Fang, Thom é H. (Fang, Thom é H.) (1899–1977) foxing ἃ⿏ buddha-nature 174 CHINESE-ENGLISH GLOSSARY Phonetic Rendering(s) Chinese Characters English Rendering gong ℔ public Guomingdang (Kuomintang)⚳㮹源! !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Hanyu Shenxue / 㻊婆䤆⬠ / Sino-theology / Sino- Hanyu Jidu Shenxue !㻊婆➢䜋䤆⬠!! Christian Theology he harmony He Guanghu ỽ㺔! ! He Guanghu (1950–) He Shang 㱛㭌 River Elegy (1988 CCTV documentary series) hexie shehui 媏䣦㚫 harmonious society Hong Xiuquan 㳒䥨ℐ! ! Hong Xiuquan -

Naismith's Hamilton Directory for 1878-79
Begbie's Pure Fluid lapesia. THE valuable properties of Magnesia have been long and uni- versally known. The use of Magnesia in the solid form has been very properly objected to, on account of its tendency to form dangerous concretions in the bowel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luid Magnesia has removed this objection, as it has been proved by eminent naedical authorities that the use of this favourite Medicine in the liquid state is not liable to produce these con- cretions. It can therefore be used with perfect safety and incal- culable benefit by anyone, and is specially adapted for Adult Females and Children. This preparation is deservedly esteemed, possessing as it does all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Magnesia, with more immediate action, and being administered in a more elegant and convenient form. The continued use of Soda and Potash as antacids has been known to produce very serious results in the system. These agents can be entirely dispensed with, as the Fhiid Magnesia is a more efficient remedy, and is perfectly free from the danger of causing injurious effects. MANUFACTURED BY GLOBE COMPANY, Manufacturing Chemists, Commercial Road, Glasgow. London Depot—8S Lea denhall St. , E. C. Sold by all Chemists and Druggists. Crawford's JSm Watclies. Being the only Manufacturer in Scotland of Chronometer, Duplex, and Lever Watches, he can recommend all Watches sold by him. First-class Silver Patent Detached LEVEE WATCH, 4 Jewels, Gold Balance, Enamel dial, Glossed and Polished Pivots and Shoulders, made in sizes to suit Ladies and Gentlemen, only £4 4 First-class Sterling SHver HORIZONTAL WATCH, 8 Holes Jewelled, Gold Balance and Enamel Dial, made in sizes to suit Ladies and Gentlemen, only 200 Would call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Watch. -

British Missionaries?
British Missionarie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 1807-1966 A paper presented at “Missions, Modernisation, Colonis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Seven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Oslo University, 6-13 August 2000 Wong Man Kong, History Depart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s how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hristian missionary work in Asia in particular and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general. It can be represented in a pendulum metaphor, swinging between “incorporation” and “rejection” as the two ends. It seems unlikely to identify a case showing a total incorpor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a non-Western society. Neither is there a case of a total rejection.1 This pendulum did not exist in vacuum. The general trends in modern history that nee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clude the non-Western world’s search for modernisation along with the lines of colonisation/ decolonisation. Thanks to Andrew Porter for he pointedly demonstrates the limit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as a conceptual tool to explain missionary experience in modern history.2 In this paper, the modest intention is to offer some points of departure on how the pendulum situation was like in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modern China in which British missionaries’ presence played a role. The Chinese search for modernisation in the wake of the coming of Western imperialism (or simply colonisation/ decolonisation) has been a major theme of much serious scholarship. However, not much has been done on the role and impact of the 1 This issue was first suggested and quite convincingly argued in Harold D. -

Fowler's Commercial Directory of the Principal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SlCSZf2_ A y^ %<\ FOUNDED BY SIR PETER GOATS, IS/O. REFERENCE DEPARTMENT ti 79 ^ No Book to be taken out of the Room. 2 223135 21 Digitized by tine Internet Arciiive in 2010 witii funding from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fowlerscommerc183637unse izzsmzi FOWLEE'S COMMERCIAL DIRECTORY OF THE PRIIVCIPAIi TO^I^l^S AlfB VIIiliACJES IN THE UPPER WARD OF RENFREWSHIRE, FOR 1836—3T; CONTAINING AIS AliPHABSTICAIi JLIST OF TRM Mtvtljmxt^, Cratrtr0, iWattufacturers, AND ALSO A COPXOUS STREET GUIDE OF PAISLEY, AND AN APPENDIX, EIGHTH PUBLICATION. t-4 PAISLEY: PUBLISHED AND SOLD BY G. FOWLER, BOOKSELLER. C-Jee next page.) ADDRESS. G. FOWLER in presenting to the Public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Directory, returns his sincere thanks for the prompt and valuable as- sistance rendered to him by numerous Gentlemen in the County. Also, to those who have now become Subscribers, and others who have sup- ported the Work since its commencemeiit. He now begs leave to remind the Public, that being first induced to i-.y^Mnence the Work at the solicitation of a mimher of the most respecta- o/? Merchants and Traders in the Upper Ward of the County, (and ./r . the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Upper Ward ivas produced, he was solicited to extend his Work to the Lower Ward, by the Merchants and Traders there.) After so many respectable solicitations, he pledged himself to Publish his Directory for the Upper Ward -of the County annually, for six pub- lications, which pledge he has redeemed. He now respectfully announces that the Work will be Published every two years for other six publications, provide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sub- .fcribers is obtained, so as to insure him a proper remuneration for his labour.